科技是救星还是终结?

文/ 道格拉斯·库普兰 美国著名作家
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未来出现,却从未真正觉得曾身在其中。但就在刚过去的一年,几乎是一下子且无法否认地,所有人都神奇地、共同地生活在了那个遥远的、曾被称为“未来”的地方。“未来”来到了我们身边,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有人对你作了个恶作剧,但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一直在等待恶作剧被拆穿,它总是一副即将被拆穿的样子,但永远不会真正被拆穿——这就是未来。
是什么将我们从现在带走,抛进了未来?是太多发生的太快的变化吗?是很多朋友向我们显摆一款价值99美分,却一下子淘汰了工业中心地带剩余的几千个工作岗位的炫酷新应用吗?也许将我们抛进这未来的是太多反常天气;又或许是几乎完全取代了电话通话的短消息;还可能是安吉丽娜·朱莉防患于未然的乳腺切除术;抑或是一部关于朝鲜的幼稚喜剧,它几乎引发核战;还有可能是《查理周刊》(Charlie)事件。这多奇怪:未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被迫的意识决定的,即意识到有许多人不想有未来或不想要未来。他们想要的是永恒。
我感觉自己正置身于未来,是当我看到某个酷炫事物,而看到它与我伸手去掏iPhone想把它拍下来的间隔时间缩短到了约两秒钟,而不是几年前的30秒钟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正置身于未来,是每当我在网上寻找某种东西的图片,却发现我看到的半数图片都打着水印在出售的时候。
这种未来感会持续多久?它会是暂时的吗?也许社会将自发地进入一段科技停滞期,让我们的脑细胞放个时间假,感觉它们是在1995年,而不是2015年。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事情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
置身于未来的生活健康吗?大概不算健康。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山洞里,对改善人类生活毫无概念。我们并不是真的天生适应不断的高速变化。既然如此,是否存在一个集体爆发点?如果是,那么这个集体爆发点会是什么样?它或许不会是一次集体的政治社会表达,比如一场暴乱或公投。它或许是某天早上我们所有人醒来,然后意识到我们不是中产阶层或工薪阶层或任何阶层……我们基本上只是存在着,而互联网让这种存在变得可以忍受。
最近有人问我,“从长远来看,科技是我们的救星还是我们的终结?”我仔细考虑了,问题在于,科技是我们发明的。科技仅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表达,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外星人送给我们的什么东西,然后出问题时我们可以责怪科技。我们真正该问的是,“人类会毁灭自己吗”?无论是在10年前,2000年前还是1000年以后,答案都是同一个。我们仍存在着,因此答案是不会。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受困于“生活在未来之中”,在这里我们受困于在醒着的每一刻为这个问题担忧。
我们的大脑最多能接受多少“未来”而不爆炸或崩溃?我在想,这种未来感是不是一种某个时间段结束前出生的人才有的精神记号,一种专为记住一个曾经拥有现在时的世界而存在的心理状态。千禧一代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需要抛弃,没有什么可引发忧愁,没有什么需要忘记。我为最近的一场博物馆展览制作了一批T恤,上面印着“I MISS MY PRE-INTERNET BRAIN”(我怀念我前互联网时代的大脑)。我们让一些17岁的模特穿着这些T恤,然后拍了照,每个人看到都哈哈大笑。
我努力去想象一个没有现在时的世界,一个时间永远距现在5秒钟的千禧世界,我几乎找到了那么点感觉。我怀疑在一个永恒未来的世界里,为了心理健康,放弃前互联网时代大脑才是唯一明智的适应策略。当年拓荒者们穿越北美洲大陆,一路留下不要了的钢琴、沙发和梳妆台,在朝着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前进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减轻负重。我想起曾读到过的拓荒者的故事,他们被困在一场森林大火里,淹没在沼泽里、用芦管呼吸空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剩余的过去化为灰烬。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我们淹没在泥浆里,等待大火熄灭,等待进入一个更轻盈的、崭新的世界,一个很可能要从零开始重新建设的世界。
(原载于《金融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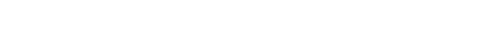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