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因为我们是上等人?
撰文/蓝军 编辑/刘昭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年)不久后的英国,一位名叫约翰·波斯托克(John Bostock)的医生发现自己每到夏天就得一种怪病——眼睛奇痒、不停咳嗽、打喷嚏。
出于职业敏感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兴趣,波斯托克在致伦敦医学外科协会的一篇论文中,将这一奇怪病症命名为“夏季黏膜炎”。
这个古怪的病名,如今鲜为人知,替代它的词则家喻户晓:花粉过敏。

▲约翰·波斯托克饱受花粉过敏之苦。为缓解症状,他尝试过放血、催吐、冷水浴、服鸦片,无一奏效(图片来自网络)
贵族病的不列颠入侵
“夏季黏膜炎”患者非常罕见。从1819到1828年,波斯托克只找到28名病友。有趣的是病人无一例外出身英国上层阶级。
半个世纪后,波斯托克的后辈查尔斯·布莱克利记录道:患有“夏季黏膜炎”的病人几乎都是教士和医生,就算不是上层阶级,也至少受过良好教育。看得出,这个病不忘初心,对患者依然挑剔。
唯一的“好消息”是:它终于走出了国门,令英国绅士不再孤单。
19世纪中后期,法国、德国、瑞士也陆续发现相似病例。由于只在夏季制作干草的时节发病,欧洲人把它称作“枯草热”。欧陆医生的诊疗经验与英国同行类似,“枯草热是贵族病”的观点由此成为欧洲医学界的共识,新大陆也不例外。
既然是贵族病,显然足够有钱才能享受到“休假式治疗”。曾被林肯派往欧洲、作为合众国总统特使的教士亨利·毕彻公开宣称:对于能加入枯草热病友协会、拥有去豪华度假区休病假的机会,“我非常感恩”,度假区的夏天是如此安逸,以至于“我不能痊愈,也不想痊愈”。
毕彻所说的枯草热病友协会,正是美国镀金时代上流社会最显赫的社交组织之一。任何枯草病患者交1美元就能入会(那时1美元的购买力可不低),会员不外乎医生、商人、法官、律师和政府高官。
最著名的度假区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白山。这里原本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自从时任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枯草热症状在此缓解后,白山的旅游业和酒店业迅速崛起。

▲ 白山枫木酒店(Maple wood)。19世纪70 年代后,白山兴建了许多类似的豪华酒店。这些酒店的主顾都是美国东北地区的城市 富裕阶级。艾默生、梭罗和其他许多文人,也曾靠描写在白山躲避花粉的岁月引起广泛关注(图片来自网络)
盛夏六月,新大陆又到了社交的季节。东北工业区的富商巨贾,逃离纽约和波士顿,来到豪华度假区休假。他们六个星期的度假支出,抵得上普通工薪阶层半年以上的工资。
可不要以为当时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低,故而富豪们花钱也不太多。仅以肉类消费为例: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黑人奴隶的肉食配额是平均每周3磅猪肉,两倍于法国平民;而当时美国农民在遗嘱里指定留给寡妇的肉类供应每年超过200 磅。
毫无疑问,大量高净值人群的养生度假游,带动了沿线铁路运输业和经济发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威廉·哈德得意地宣称,至少在枯草热方面,美国已比英国遥遥领先:
全世界只有美国建立了专供枯草热患者的疗养胜地;只有美国的铁路运输公司,为了满足枯草病患者度假而产生的运力需求,要向政府申请资本化;只有在美国,枯草热才创造了这么多工作机会和经济繁荣。共和党简直应该把枯草热写进施政纲领。

▲19世纪时,花粉过敏者为了“保命”,不得不戴上特制的面罩(图片来自网络)
过敏不只是因为我们查得勤
如果推广至更一般的“过敏”,至少今日已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的专利。世卫组织估算,全球超过20%的人口都有过敏反应。不过,依然存在的现象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越高的国家,过敏问题就越严重。
在欧洲,对普通人过敏的流行病学调查始于20世纪初;最晚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学界和医疗机构,都对国民过敏情况进行了大范围、高频次、多维度的监测和研究。
研究越多,问题越大。过敏发病率在近年的增长速度远超医学界预期:过去十年,欧洲医院接诊的严重食物过敏儿童人数增长了700%;英国儿童食物过敏率翻了一番;1997到2007年,全美18岁以下儿童食物过敏率增长了18%……
医疗和学术界的进展,很快渗入到了立法层面。近20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食品过敏原标注体系,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治理,不仅要考虑复杂的方方面面,还是高度技术性的活计。
欧盟和日本列出了麸质谷物、鱼类、花生、牛奶等7至14种强制性标注过敏原;美国也列出了8种,但由于美国的法案未对非包装食品和餐厅做出强制标注要求,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
在学术研究、医疗检查、行业标准、政府保姆的伺候下,发达国家公众对过敏的认知度自然也就更高。甚至在社交中形成了规范:即便参加小型午餐会,主办方也会提前询问与会者是否对特定食物过敏。与中国人以“吃了吗”来寒暄不同,“你不吃什么?”才是许多西方人喜闻乐见的社交话题。
另一个世界,情况则大不相同。直到 2012 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任何居民食物过敏的数据,更遑论为食品过敏原立法。
是否由于数据、研究的匮乏,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过敏情况被严重低估?而发达国家是因为查得勤所以才过敏多?
从现有的少数对比实验看:中国人的身体确实没那么敏感、娇贵。
儿童哮喘与过敏国际研究(ISAAC)发现:患病率最低的是东欧和亚洲(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中国、韩国),最高的是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欧洲最大的临床免疫学组织对比了中国内地、香港、瑞士、美国50岁以上成年人的哮喘患病率,也发现中国内地居民患病率最低。
然而,就连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民,也经不起祖国特色美食和医药的偷袭。
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显示,炸昆虫(蚕蛹、蝗虫、金蝉)、菊花茶、野菜、牛蛙、甲鱼、中药,都是中国特色致敏原。它们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发现13例(13/288)患者因注射中药注射液死亡。

▲1906年,维也纳医生 Clemens von Pirquet(左) 创造了“ 过敏”(Allergy)一词。此后一百年,过敏成为了全球性的疾病体验(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为什么富裕的现代国家过敏更严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富裕的现代国家过敏越严重?又为什么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富裕地区居民的过敏更严重?
学界尚无定论。其中一种被普遍接受、获得众多研究数据支持的“卫生假说”认为:
急剧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导致人体不能接触足够的病原体,免疫系统无事可做。而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环境中有一定数目的病原体,当病原体达不到这个水平时,免疫系统就会攻击与其接触的无害物质,导致良性微生物(如花粉)引发的免疫反应。
换句话说,卫生条件越好,幼年时期接触各种微生物 / 病原体的机会越少,免疫系统不能像祖辈一样“正常”发育,则长大后出现过敏性疾病的几率相应增高。
当然,相关不等同于因果。“卫生假说”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同时也有其他理论被提出用以解释过敏性疾病的流行。
例如室温、湿度升高利于尘螨等室内过敏原滋生,而人们生活习惯改变,户外运动减少,增加了和室内过敏原接触的机会;还有精神压力、污染、遗传因素等等,都可能是导致过敏性疾病越来越普遍的原因。
所以说,小时候玩玩泥巴,接触一些小猫小狗,“脏一点”让免疫系统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长大后身体不至于遇到一点异物就大动干戈,这样人体会更健康也不一定呢。
与时俱进的“阶级病”
近代史上,许多在当时无法用科学理论解释的疾病,都曾被人们看做“阶级病”。
最典型的例子是肺结核。十八世纪中期,肺结核在欧洲流行。死亡率极高,病因不明。时人判断女子是否易染结核病的方式之一,便是看她对异性的吸引力有多大。越美的越容易得肺痨。这是因为肺结核使人苍白、消瘦、瞳孔泛光、脸色潮红,契合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审美。
除了长得好看,想得肺结核还要出身上流。与花粉过敏一样,肺结核专属那些耽于情感、不计后果、惯会风月、奢华文雅的上流人物。

▲病床上的肖邦。肖邦一生被肺结核折磨,法国作曲家圣桑曾写道, “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是健康不再时髦之际。”(Teofil Kwiatkowski, 1849绘)
在细菌学说和免疫理论兴起之前,西方生物医学界将疾病视为病患独特的生命体验,每种病症都是“个性化的病理现象”。文人受其影响,便认为“强健的身体都是一样的,老弱病残各有各的美好”。
没错,是美好。比如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就说:“关于健康的理想只在科学上有吸引力,真正有趣的是疾病,那是个性的一部分。”托马斯·曼更在《魔山》中直言: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生理疾病是由细菌、病毒或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起的。医学进步,让浪漫化生理疾病越来越难。今天,只有精神病才能自带阶级感。拖延症、强迫症、躁郁症,似乎专门袭击那些寄居在键盘上的有闲阶级。
百年不变的唯有一件:生病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事情。■(本文转自“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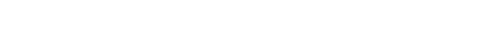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