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教我们的生死观
编译 李薇濛 编辑 丁林
作者简介

Haider Javed Warraich:美国杜克大学心血管医学研究员、《现代死亡: 医学如何改变临终》一书作者

作为一个医生,我有时会在临终患者的房间里送他们最后一程。患者的家人们会围在病床旁,每个人都看着我,等着我说些什么。这些人的人生阅历都比我丰富许多(我常是病房里岁数最小的),但他们却对死亡一无所知。
比起消防员、警察或军人,医生这个职业见证着更多的死亡。但医生们通常认为,死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它是待办清单上的方框,图表中的数据,或者临床试验的结果。对医生来说,死亡是世俗的、枯燥的、单调的,而且与医学中的很多概念不同,死亡是极端二元化(非此即彼)的。因此,医生会把死亡当作一种概念或过程看待,而不是常人眼中的一种现实或人生“终点”。
医学的进步,改变了人类临终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始终在寻找一个复杂问题的终极答案——什么才是“好的死亡”?
在我们的祖先看来,暴力事件或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总是突如其来,无法预测。到了现代,医学的进步催生了一个崭新的生命阶段,称为“临终”。处于这一阶段的患者由于无法治愈的终末期疾病,需要在疗养院里看护——其实直到不久的过去,我们才发展出这样的生命形态。
20世纪,人类历史见证了死亡概念的巨大发展和变化。生物医学的进步不仅改变了生态学、流行病学和死亡经济学,甚至也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改变了死亡的内在含义。如今,生与死的界限不仅没有变得清晰,反而更加模糊。如果不进行成套的实验,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一个人是死是活——现代医学所产生的生命维持技术,几乎能让我们的躯体永远生存下去。

▲生存还是毁灭?如今这是个“技术问题”
很多人认为,能够“自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失为一种好的终结(善终)。如果要描绘一场“自然死亡”,我们应该会想象一位年迈的老人躺在家里的病床上,气息奄奄、眼神涣散。眼含泪水的爱人、子女围坐床前,紧紧握住他/她的手,直到病人的最后一口气咽下,永远告别自己深爱的世界——这是文学作品中万年不变的写作套路。法国死亡学与社会史专家阿利叶(Philippe Ariès)在其所著的《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人对于死亡的态度》一书中写到,临终告别的场景“是由病人自己组织策划的。他主持了这场活动,他知晓活动应有的礼仪”,死亡是一次公开的仪式,“父母、亲友、邻居都必须到场”。
虽然现代文学和流行文化依然很热衷于描述这样辉煌壮丽的死亡场景,但它们最好还是老实待在虚构世界里。文学家的“自然死亡”场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描绘的是在现代生命维持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死亡情景,它仅仅是对那个年代的社会和科学背景的反映。
当今社会中,技术已经占领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的渴求,反映在对自然分娩、自由旅行和绿色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上。人们对于“自然”的渴求,同时反映出对技术的明确反抗。
当人们表现出“自然死亡”的愿望时,他们其实在暗示:让生命的最后阶段尽量少些技术的陪伴。医生们也默契地沿用了这种说法,当他们想暗示家属,更多的治疗可能已经徒劳无功时,他们会劝说家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人们对于医疗技术的看法,主要基于它们所达到的结果。如果通过使用药物、设备或进行医疗程序成功避免了患者的死亡,技术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奇迹”;反之,如果死亡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家属就会认为技术的介入让死亡变得“不体面”了。
综上所述,是否“自然”地死去,是人们眼中对“善终”的评判准绳。
细胞层面的生死循环
或许我们需要观察一些更为基本的事物,才能理解到:如果把死亡从社会的语境中剥离开来,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本质。或许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在构成所有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生命基础的小小细胞中就能观察到。
每周四上午,我所在的医疗团队都要占据心脏移植手术室里前排的席位,见证显微镜头下史诗般的战争。巨大的屏幕上显示着一幅幅静态图像,图中是从刚做过移植的患者心脏上剥离的小块组织。这些组织细胞呈粉红色,被不同数量的蓝色免疫细胞所包围、攻击。
蓝色细胞的数量越多,就愈加狼吞虎咽地啃食粉色细胞,也更清楚地告诉主治医生: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正在排斥外来的移植心脏。
这些图像描绘了生与死在极细微尺度上的一场较量。它们是如此美丽,我甚至幻想过把它们裱起来挂在家里。但是,我对这些细胞研究得越深,就越清晰地认识到:它们或许能解答当今时代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生命在最基础的细胞层面的生死事件,比个体层面的生死更复杂、更加动态,也更平衡——我们把它看作一个二元方程。我们的一呼一吸间,体内有的细胞分裂出了新的生命,有的细胞则收到死亡的信息。所以,即使作为个体的我们活着,身体内也总有一部分在不断死去。虽然科学家了解细胞的分裂、诞生过程已经百年有余,但是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揭晓了细胞的死亡过程——细胞有三种死亡机制。
最丑陋、最不优雅的死亡形式是细胞坏死。由于缺乏营养或受到有毒物质的损害,坏死细胞最终将发生破裂,并将内容物释放到血液中。在心脏移植过程中,由于排斥反应发生的细胞坏死,会引发机体的强烈免疫反应。因此,坏死就可以视作细胞版本的“不得善终”。
细胞死亡的第二种方式是自噬,即细胞将自身有缺陷或多余的成分变成营养物质并循环利用。在营养供给有限但未完全中断(例如心力衰竭)时,细胞自噬就会发生。
但是,最复杂的细胞死亡方式“细胞凋亡”(apoptosis)与前两种方式都不相同。凋亡是一个希腊词汇,原用于描述树叶的凋落。
凋亡是一种程序化的细胞死亡方式。当细胞老化或开始受损(通常由信号分子推动)后,就会进行受控的自我破坏过程。与坏死不同,凋亡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给免疫系统增加负担,而是安静地自行萎缩、溶解。细胞凋亡是控制我们的肠道等器官不会无限生长的重要生理机制。
凋亡对生命的意义
细胞凋亡的意义对于“死”固然重要,对于“生”更为关键。主动凋亡的机制不仅对个体的存续有利,甚至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衍生息也至关重要——秋天的落叶能为树木补充养分,让它来年继续绿意盎然。比忘记了如何生活的细胞更糟糕的只有拒绝死亡的细胞。
我们人类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获得永生,但永生现象在细胞世界中早已存在——癌细胞。事实上,许多癌症都是由细胞凋亡机制的缺陷引发的,而大多数新型癌症疗法的设计思路,也都是使细胞凋亡恢复正常的程序。
人类对于提高平均寿命的不断尝试,取得了与细胞层面“癌症”类似的效果,并改变了现代人死亡的宏观远景。我们与老龄化、疾病和死亡的持续斗争,给社会和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很多方面,细胞层面的生命和死亡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要比人类个体层面的生死更加深远。对细胞来说,一种物质如果对它所属的生命体有益,就是对它有益。尽管细胞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生存,但是它们的适当死亡,对于生物整体的生存至关重要。其实,许多生物个体也为了自己的群体的利益,以类似的方式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人类总是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否认死亡,但死亡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如果真有敌人,也应该是由死亡所引发的恐惧——这种恐惧常常引诱我们去公然反抗自然的约束,妄图成为超自然的存在。然而,一心追求永生的人往往难以避免像细胞坏死一样的命运,他们殚精竭虑,动用无数资源,最终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追求无意义的永生,远远不如细胞凋亡来得宁静安详。即便我们想要违抗死亡,细胞也已经现身说法,用触目惊心的癌症告诫我们,即使只有十亿分之一的细胞能达到永生,对于生物体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永生是否“自然”?
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Robert Horvitz曾经所在的研究组发现了细胞凋亡机制。我问他,细胞死亡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启迪?他的一句回答切中要害:“在你之前,只有一个人跟我讨论过细胞死亡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可能联系。”为何芸芸众生终日忙碌于生活,却鲜有人思考死亡的真正意义?
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下,细胞凋亡的对等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先找到细胞坏死在人类社会中的对等机制。
我的经历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躺在医院里,浑身上下连接的设备比钢铁侠还多(人工呼吸机、营养或透析机等生命维持设备),而他大脑苏醒的几率微乎其微,这种情况就可以认为是“坏死”。而如果病人在临终之前拒绝医院的心肺复苏或插管治疗,或者在家里选择临终关怀服务、使用医师的处方,就与细胞凋亡更加类似。
我们总在无休止地求索,希望能够解答生命中那些重要的问题,却常常忽视了在生命的基础机制中寻求答案。细胞凋亡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它代表一种纯粹的死亡观念,我们或许应该考虑将这种观念加入自己的死亡观中。
细胞凋亡引出了一个终极悖论——生物体若要生存,个体细胞就必须死亡,而且一定要以优雅的方式离去。“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是凋亡太少。在这些情况下,激活细胞凋亡机制,反而可以延长机体的寿命。”Horvitz对我说。
细胞对于死亡的理解比人类更清晰。它们知道,一旦某些个体的生命超过了寿限,就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虽然人类渴望永生不朽,但细胞告诉我们:没有死亡的生活才是最不自然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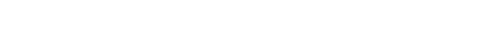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