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头术”面临伦理争议
异体头身重建仍有很多实际问题有待实验,从而在临床实施上拿到更大的把握,这是横在将要参与到此次异体头身重建手术的人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困难。
然而,“换头”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很多争议,甚至演变到了一片口诛笔伐的状态。
争议一:手术风险大,不成功就是“谋杀”任晓平:不做,永远都不可能成功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专家王长希教授对所谓的“换头术”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从技术上不可行,“这是无稽之谈,百分之百失败的手术,以后肯定是个笑话。这样的手术太超前,没有可能成功。而且,即使接受手术的病患本身同意,也涉及谋杀,在伦理上更加不可能。”王长希说。
“我觉得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评价‘换头术’只是艺术家的想法,同种异体脊髓的功能重建和再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将是两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瑞典留学归国的器官移植医生、厦门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齐忠权如是评价,“目前没有科学数据支持脊髓再植可以成功,更何况异体移植。如果耗费巨资把目前所谓换头‘适应症’患者治疗成一个高位截瘫或近乎高位截瘫者,且需要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医学界的同行不会达成共识。”
“这是不是一个愚人节玩笑?”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伦理学家翟晓梅听到此事的第一反应,“要不就是在炒作。”在她看来,这一手术风险很大,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翟晓梅认为,如果手术是为获取科学知识,那是为了将知识应用在其他人身上,这时就必须做利益风险评估。如果是为了在临床上解决患者的问题而采取创新性疗法,翟晓梅说,那也需要提供“有道理的方法”,“不是科学家自己说有道理就行了,必须是医学共同体公认的道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则把这件事情称作“人体的登月工程”。头和躯体结合之后,还是不是头来主宰整个人说不清楚。“美国有科学家称细胞是有记忆的,如果细胞有记忆,躯体会有独特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和大脑是不匹配的。此时,他的大脑和身体就会出现矛盾。”
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神经外科教授戈德史密斯则表示,这个换头计划规模太大,潜在问题极多,非常难实行。美国神经外科协会专家巴杰则直抒胸臆:“我不希望任何人做这种手术,这比原样儿病死还糟糕!”
面对一片声讨,记者在任晓平的眼中看见的是一份坚韧,态度也显得非常笃定,“技术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果不做,那么永远都不可能成功,我们一直尝试着不同的方式去将各部分进行完善,从事这方面研究,就是为了让技术达到最佳”。
任晓平用世界首例心脏移植举例,“心脏移植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但是现在仍未完善”,1968年1月9日,南非医生克里斯琴·巴纳德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然而患者仅生存了两周,“但是正因为巴纳德医生的举动,才开启了人类器官移植的大门,没有当时的两周,就没有随后的两个月、两年,甚至是二十年”。中国医师协会曾发表文章表示,在医学史上,巴纳德医生的举动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它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所带来的社会意义也许比它在医学上的意义还要重要,它使所有器官移植手术都成为了可能。

争议二:“换头”后如何区分头和身体?任晓平:人的生命至高无上
从本质上来,异体头身重建或将成为人类医学发展的里程碑,手术将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对参与人员、或者说医学技术水平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然而技术难题可能并不是摆在手术面前的最大障碍,医学伦理上的争议或许才是令研究人员最头疼的。
记者曾就基因编辑人类胚胎问题向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发出过采访邀请,他因为首次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以探索治疗地中海贫血症的新途径而获得《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人物,但是黄军就以“想要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邀请,这或许只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军就的研究工作不仅收获了奖项,也将一片“伦理声讨”收获囊中。
而此次的人类“换头”同样被套上了伦理枷锁。“头接上后,如何去区分头和身体的归属,临床上没有这样的案例”。齐忠权说,换头或者换躯干,无论从患者心理还是医学和伦理学方面,都是难以接受的。“意大利出了很多艺术家,但我们是科学家。”
齐忠权所提出的伦理争议并不是一家之言,“换头”消息的披露不仅引发了技术争议,在伦理方面的声讨也喧嚣尘上,诸如“换头之后究竟是‘谁’”“如果对身体不满意,是不是还将再换”等问题不断浮现,甚至不乏一些宗教人士将科学研究与教义、神话相连。
面对伦理争议,任晓平回答得非常直接,他提供给记者很多英文的文献,“这些很多都是国内外的专家撰文,从伦理的角度阐述人类换头的文章,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多关于伦理的内容”。他告诉记者,从伦理学方面的探讨是必要的,无论是对于公众还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但从推动人类医学技术的发展角度来讲,新生事物如果你不做,问题永远回答不完,只有你去实际地进行尝试,那么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任晓平认为,在做之前科学家、研究人员、媒体等各方面具有引导的责任,但是这样的引导作用毕竟有限,只有将实际的结果拿出来,才能说明一切。就好像百年前爱因斯坦对于引力波的预言,百年后人们才用LIGO证明其真的存在,但是在LIGO建设之初真的能够确信会观测到引力波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争议三:伦理学阻碍科学发展 任晓平:面对生命,伦理要让步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质疑、争论变为实际的过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这样,一切都准备就绪,再进行实际的操作,得到一个百分百确切的答案,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每个科学进步都伴随着一定的质疑和争论发展而来,倘若你不做,这项科学就会停止。”任晓平告诉记者,头部移植被学界束之高阁已经近半个世纪,早在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怀特博士及其助手就首次为灵长类动物恒河猴施行了换头手术,接受手术的恒河猴存活了8天,不仅存有意识,而且可以吃东西,眼睛还可以跟随人在室内的走动。
“怀特做了一辈子的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伦理问题以及社会的一些偏见、宗教的阻碍,最后使得科研停滞。”任晓平回忆这位在他眼中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时无不惋惜。
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医学在技术上要比怀特时代发达许多,但是当时怀特面临的伦理等阻碍却仍然存在,今天头部移植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如果再阻碍,可能十年、百年之后,这仍将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
任晓平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伦理学是个行为规范科学,面对病人的生命,伦理学必须要让步。如果一个技术可以有效延长人的生命,伦理学角度没有理由不批准。对于新事物,伦理学可以制定一个规范,让新技术在这个框架以内进行,但没有道理阻碍科学的发展。“我认为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个基础上,伦理学的一些规范可以帮助临床实践”。
怀特曾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开篇写道:“在人类器官移植领域,人们取得了很快的进步,从肝、肺、心脏、肾到最近双手的移植都成为了现实,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一件以前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移植人类的大脑。”怀特预言,移植大脑将在21世纪初期成为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做好了移植头颅的准备呢?一些技术条件的确业已存在。”
诚然,怀特的预言在时间上似乎非常准确,但是其所面临的阻碍却随预言一样绵延至今。■
Tips 第一个“换头”志愿者:瓦勒里·斯皮里多诺夫
第一位自愿接受全球首例“换头手术”的志愿者名为瓦勒里·斯皮里多诺夫(Valery Spiridonov),已经年满30岁的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位俄罗斯的计算机工程师,他患有Werdnig-Hoffmann病,也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这种疾病会导致患者的肌肉停止发展、退化,这令他自小全身伤残,骨骼畸形,而脊髓性肌萎缩目前尚无治疗方法。
斯皮里多诺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表示:“我对科技很感兴趣,对任何能够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进步也很感兴趣,无论结果如何,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还能为子孙后代奠定一个科学基础。”他相信,这台手术将帮助他延长生命,同时也将给科学研究带来巨大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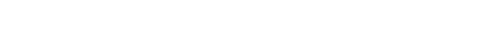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