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还是自责:中国领先争议性研究?

中山大学学者黄军就的论文顺利发表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

身在美国的杨璐菡在强大的舆论和社会压力下中止了研究

2010年,当生物狂人克雷格·文特尔首次人工合成生命体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忧,人类已经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创造万物,担心该技术一旦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中国还没能在科学前沿领先,却率先开拓在伦理上极具争议性研究的前沿。我们应该自豪还是自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日,身处中美两个不同实验室的中国年轻科学家,在极具竞争性的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从事着“异曲同工”的科学研究:利用同样的基因编辑技术,尝试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进行修饰,但双方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身在美国的杨璐菡在强大的舆论和社会压力下中止了研究,而中山大学学者黄军就的论文得以迅速顺利发表。我们应该自豪还是自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两篇对人类胚胎基因“动刀子”的文章
正在哈佛大学著名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杨璐菡,近来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细胞基因进行修饰的研究尚未发表,就遭受到科学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和压力。
这位不到30岁的哈佛女博士后不仅拥有北京大学双学士学位(生物学和心理学),2014年还入选了《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医疗领域“30位30岁以下俊杰”荣誉榜单。除此,杨璐菡还与其导师丘奇成立了一家研发以及商业化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
事实上,她在生物学领域的天分在高中时就被挖掘出来,2004年她参加了“第15届中学生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并荣获金牌。但这一切仍然未能阻止人们对她这项研究提出尖锐的批评。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近日对乔治·丘奇实验室的一则报道披露,杨璐菡正在对人类尚未成熟的卵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其中包括了对生殖细胞BRCA1突变基因的改造。这项研究计划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可剔除掉BRCA1突变基因,从而让那些和著名演员安吉丽娜·朱莉一样携带有BRAC1突变基因的女性,降低其下一代可能患上乳腺癌的风险。报道刊发后,杨璐菡的研究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止,论文发表变得遥遥无期,对该实验的恢复也没有日程表。这一事件让杨璐菡变得谨慎起来,她不再愿意向外界透露有关自己的这项研究。
相比之下,中国中山大学学者黄军就研究团队显得十分“幸运”。日前,该团队进行的类似研究,并没有遇到社会舆论以及伦理禁忌的压力,文章顺利发表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
黄军就在这篇文章中指出,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动物细胞以及人类细胞基因修饰,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中潜藏着巨大价值,为了弥补该项技术在人类胚胎基因修饰上的空白,以及证实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植入前胚胎基因修饰中的价值,他们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三原核合子(不能正常发育的胚胎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将其携带的β-地中海贫血突变基因剪切掉。最终他们得出结论,目前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尚不能进行临床应用,因为仅有1/3的胚胎细胞基因得到了修饰,如果将该技术应用于临床试验,这一概率需要接近100%。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善”后代或是不归路
事实上,不少学者纷纷表示,应禁止该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的改造。因为对这项技术的掌握程度,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尽管研究者目前可利用这项技术来修饰细胞的基因,但它同时也有可能会剔除有用的基因。技术目前还有很多短板,研究者在小鼠、牛、羊以及猪等哺乳动物身上的试验,均发现这一技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CRISPR/Cas9技术的脱靶效应可能会在非目标位置产生非必要的DNA突变,由此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将该技术应用于生殖细胞的基因修饰,无疑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这不是对个体而是对人类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指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善’其后代是一条不归路,开了闸就是洪水猛兽,对个人表型作用来说是小事,但对人类就是大事,技术如被一些不法分子获取使用,那将贻害无穷。”
“研究中使用的胚胎安全不是核心,胚胎有体细胞和生殖细胞,改变生殖细胞是争议的核心。”饶毅表示,如果可以改变一个基因,就可以改变多个基因。人类已知的“致病”的突变基因可能有几百个,但是即使如地中海贫血病,突变基因可能对个体致病,但对群体的进化作用到底有多少好处,可能数百年内尚无法确切知道。如果人类已知的数百个基因突然人工永久改变,结果如何可以预知?
饶毅指出,即使以治疗为目的,针对生殖细胞的编辑改造仍不宜被允许,甚至相关的研究也不应得到提倡。既然“致病”基因可以改造,那么为何胖瘦高矮美丑等等一系列性质的基因不能被改造?
人性的问题并非立法可以改变。一旦立法允许,就变为政治立场的博弈。但他们不可能对人类的长远历史负责。所以,完全不改造生殖细胞的作法就是为了阻止这条路,而不是为了反对某个具体技术。
该技术在西方学术界仍有许多拥趸
不过,这项技术在西方学术界仍有许多拥趸,如乔治·丘奇,他是基因编辑技术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此外还有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专家乔治·大理(George Daley),他在评价黄军就这项研究时称:“这是CRISPR/Cas9技术应用于人体胚胎细胞基因修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它向人们显示了未来在根除致病基因方面具备的潜力。”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遗传学家黄行许,以及美国加州拉荷亚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发育生物学家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都是这项技术的坚定支持者。2014年年初,黄行许等学者利用CRISPR/Cas9技术对猴子胚胎细胞进行了基因编辑,获得了两只健康的“基因编辑猴”,当时他的研究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担心下一步该项技术会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上。现在看来,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黄军就研究被《自然》《科学》拒绝
黄军就原本希望将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但先后被拒绝,最后发表在并不广为人知的刊物《蛋白质与细胞》上,然而这篇论文引起的关注度绝对不亚于来自CNS(指Cell、Nature、Science)三大顶级期刊的重磅研究。对人类生殖细胞(包括精子、卵子以及受精卵细胞)基因“动刀子”,在社会伦理严苛的西方国家极具争议,因此黄军就的论文一经发表,西方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引发争议。
目前,已有40个国家不鼓励或禁止生殖细胞基因修饰研究,西欧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禁止生殖细胞的修饰。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颁布法律明令禁止这项研究,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重组DNA咨询委员会明确表示:“目前人类尚不能进行生殖细胞修饰”,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也不会支持生殖细胞基因改造的研究。
事实上,在美国,即使是对人类体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也必须得到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以及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许可。而对人类生殖细胞的修饰,美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来进行监管,并为它可能带来的风险提供相关的信息指示,开展这样的研究因此极具争议,通常是尚未进行就被社会舆论和伦理组织“叫停”。
中国对基因治疗技术包容的尺度较大
中国目前并未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约束,但对基因治疗技术有明确的规定。2009年,卫生部印发《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将基因治疗技术定义为“第三类医疗技术”,属于“涉及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的医疗技术,因而基因编辑技术或许会纳入到基因治疗技术领域中进行监管。不过这一规定仅适用于临床试验,对于基础研究,中国对基因治疗技术包容的尺度较大,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的“天花板”加以限制。
另外,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在对待人类胚胎细胞研究上态度有所不同,中国支持治疗性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坚决反对生殖性胚胎干细胞研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对这两项研究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这或许是黄军就此项研究得以站在国际前沿的关键所在。
正因为涉及到人类生殖伦理的问题,黄军就的这项研究被《自然》和《科学》杂志拒绝发表。他最终选择发表在开放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该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基本都来自中国。中国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是这本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也主要由中国科学家组成,该刊物主要发表蛋白质结构研究方面的论文。

至于这篇文章为何3月30日收到投稿,4月1日就被迅速接收,《蛋白质与细胞》编辑张晓雪称:“高效发表得益于主编们与审者、作者之间的高效交流和讨论”。不过她也表示:“根据《蛋白质与细胞》管理办法,常规审稿周期为2周,但对于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文章,经主编审阅后,可提供快速审稿流程。”
事实上,该杂志主编、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在面对《自然》的质疑时,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两天已算是相当长的时间了,你可与任何一个作者进行电子邮件交流,现在又不同以往。”
CRISPR/Cas9的主要发明者、伯克利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坚尼佛·多娜(Jennifer Doudna)却另有意见,她怀疑“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对此,《蛋白质与细胞》编辑张晓雪予以否认,她表示:“鉴于该文的学术意义和争议之处,我们不仅对其学术水平进行了严格评议,还多方咨询了出版方面和科学伦理方面的专家。在同行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高效交流和充分讨论,作者也按照我们的意见认真修改了文章。根据《蛋白质与细胞》管理办法,同行评议内容不对外公开。”
曾多年研究发育生物学和胚胎学的饶毅感到不解:“该文发表在《蛋白质与细胞》比较怪异,该刊方向是蛋白质。主编及主要负责人或许不熟悉性细胞基因编辑涉及的伦理问题,不了解其严肃性和严重性。事后,主编饶子和说两天时间足够编辑和作者进行充分交流,说明他可能没想到需要去仔细咨询熟悉伦理的专家(可以请伦理专家充分讨论后编辑部再做决定),也没有留时间以便编辑自身了解刊物应该秉持的伦理底线。”
中国像是争议性研究的前沿阵地
尽管有学者认为黄军就的这项研究意义重大,是中国科研进步的表现,但也有学者认为黄军就这项研究并没有什么创新性,该技术先后已经在小鼠、灵长类等动物身上成功使用,而他只是前所未有地突破伦理障碍,将该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上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末,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国诞生,它关注生殖技术、器官移植、安乐死、基因技术等问题,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健康乃至生死问题,这些技术的应用一直是舆论争议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开始将病毒的DNA剪切、重组,并引入到大肠杆菌中进行表达时,公众感到恐慌。1978年,当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时,美国次年就立法,禁止医生替患者培育试管婴儿,但是该法案在生效6个月之后,因被指“剥夺人类幸福权”而失效。1996年克隆羊多莉诞生,引起了全球对克隆人是否会出现的热议。2010年,当生物狂人克雷格·文特尔首次人工合成生命体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忧,人类已经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创造万物,担心该技术一旦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当克隆技术日趋成熟的时候,科学家要进行克隆人试验的声音不绝于耳。2001年,意大利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和美国生殖医生帕纳约蒂斯·扎沃斯进行的人类克隆计划,让全世界为之震惊。此后,也有其他学者公布克隆人研究计划,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生殖性克隆不仅会破坏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同时也会导致基因歧视,引起家庭伦理混乱。
近年来,中国有关生命伦理的制度规范陆续出台。2004年,科技部和卫生部颁布《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的任何研究。2007 年,卫生部发布《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其中第 27 条规定: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进行结题验收时,应当要求项目负责人出具经过相应的伦理委员会审查的证明。机构伦理委员会主要承担伦理审查、咨询和培训任务。
但是,正如山西大学学者邓蕊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所谈到,“伦理审查委员会只是披了一件伦理审查的外衣,在实践中却无法严格执行各种原则与规章”。事实上,在人类生殖伦理方面,中国可能缺乏公众监督,更多时候可能只是履行一个程序,即使出现问题,也很少有人去检查。
事实上,亚洲大多数国家科研制度以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也是让亚洲国家在这一领域屡获“突破”的主要原因。最近,对干细胞研究矢志不渝的黄禹锡与美国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发育生物学家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接受了一家中国干细胞公司93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用于合作开展干细胞研究,并将会在中国建立实验室。除了诱人的经费支持外,中国宽松的研究监管环境也是吸引科学家前来中国进行干细胞研究的主要原因。中国看起来像是这些争议性研究的前沿阵地。
黄军就等人的这篇论文在文末表示,已遵循赫尔辛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中国相关法律以及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制定的标准。《蛋白质与细胞》编辑张晓雪称:“根据《蛋白质与细胞》管理办法以及国际生命医学刊物的相关规定,作者在进行动物及人类试验时需要遵守相关规定并取得所需书面证明。本项目研究没有违反我国现有法律,并获取了相关部门的书面批准。”
黄军就所在单位中山大学在回应媒体采访时认为这篇文章没有问题,“论文引发的争议属正常学术争论”。不过有学者指出,科研涉及伦理问题事实上并非简单的学术争议,校方和期刊出版机构应该向公众公开其审查过程和依据。也有学者认为,作者单位在科研伦理制度监管方面也存在缺陷,并且 “这是一个明确的科学伦理问题,和中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差别没有任何关系。”■
(本文转载自:“赛先生”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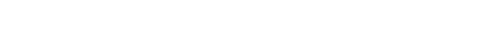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