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器人教育改造“熊孩子”

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软件才是竞争的核心,硬件可以用3D打印来制作,而软件是必须由人脑来“制造的”,把人的思维通过软件表达出来,让物品代替人去做事情。
文/记者 白竟楠
有一天放学,正在上三年级的陈紫逸抱着一个沉沉的大箱子走在队伍里,这是她在机器人课上表现优秀老师给她的奖励—一套完整的乐高。陈紫逸见到妈妈后,一边走一边叮嘱妈妈:“这是很贵的,老师说要循环使用,千万不能弄坏。”别看陈紫逸是一个小姑娘,却对机器人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学校仅有的几套乐高的使用权。
在教室里跟父母互动时,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对三年级即将到来的机器人课充满了期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向陈紫逸一样得到一套乐高的使用权,也并不是所有的小学都有机器人课程。机器人教育,正在逐渐崛起。
中国没有自己的“乐高”
郝劲峰是丰台五小的一名电教老师,至今已有14年的教龄。从2008年开始,郝劲峰建立了丰台五小的机器人社团,带着同学们从零开始,通过学生对机器人搭建及编程知识的学习,不仅锻炼了学生手脑的灵活性,开发了学生的思维,还把有天赋的同学挖掘出来,让他们参加比赛,获得荣誉。在2013年,郝劲峰通过跟学校的争取,机器人开始进入校本课程,他说:“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郝劲峰说,如果机器人课程以社团活动的方式进行,学校只有很少部分的孩子能够参与到其中,如果将其引入校本课程,机器人的知识就能得到普及,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获益。丰台五小有一套自己的机器人教学流程,课程设置分三个阶段,初期以搭建为主,让学生熟知机械的基础结构,后期以基础变成为主,能力更突出的孩子将被选入社团中,接受更深度的训练,并组织参加比赛。
目前,丰台五小只有郝劲峰一位教授机器人课程的老师,因为师资和物资有限,只有三年级设有机器人课程。很多同学在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在期待着上三年级的机器人课程,升到四年级的同学就没有机会再上机器人课了,学生家长看着孩子有如此大的热情,甚至会向学校争取,能否三年级以上都设立机器人课程。但有限的资金和师资不得不让学校暂时缓一缓这个计划。
乐博士(中国)机器人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施宏伟说,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机器人课程并没有做到本土化,主流的硬件依旧以国外的品牌为主,而乐高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看到的一组积木而已。首先,从材质来说,乐高玩具主要使用的材质是ABS工程塑料,ABS同时具有PS(聚苯乙烯)、PAN(聚丙烯腈)和PB(聚丁二烯)三者的共同特征,在性能上表现为高强度、耐冲击性、低毒性和易加工,是一种环保材质,非常适合孩子使用。其次,乐高不仅有环保的材质,还拥有系统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一套玩具,也是一个教育平台。孩子可以从低阶到高阶逐渐进步,根据乐高的教程,孩子可以自行进行编程,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拼接不同的形状。
由于国内没有系统的课程可以借鉴,学校所用的模具大多数为进口品牌,比如乐高、VEX等,除了学校购买教具高昂的成本之外,需要郝劲峰一个人去摸索出来一条符合五小教育模式的机器人授课系统。“起初我参考了一些国外的教材,但是能够直接拿来所用的内容不多,更多的内容需要自己去加工。所以整体来说,现在基本已经摸索出一条比较合适的教学模式,不过也依然在学习中教学。”郝劲峰说。
校外机器人教育“野战”
直到今天,机器人教育依然处于以比赛为目标的“散养式”模式,并且有机器人课程设置的学校很有限。
市面上零散着各种机器人教育机构,北京、上海、大连、温州等地方情况较好,这里的“较好”指的不是质量,而是数量多。由于乐高机器人教育体系的成熟与科学,大部分机器人教育机构都使用乐高,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添加内容,并以比赛和取得成绩为最终目的,用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
一位从事校外机器人教育的人士称,这就像学钢琴一样,大家都是带着获奖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能在升学中让孩子从中获益。

北京市每年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机器人竞赛,几乎涵盖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年龄段,有国内自己组建的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足球,也有从国外引进的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随着机器人火热程度的上升,每年来参加比赛的人数越来越多,机器人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度也随之升温,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也一同投入到机器人大赛当中,甚至直接从中挑选后备人才。
在首师大附中科技主任杨森林看来,去比赛化必须是未来机器人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如今机器人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不仅是机器人比赛,家长和孩子利用比赛追求短期效应已经体现在各个教育环境之中,这无意之中就会使得原本应该开源而多元的机器人教育固化,并且脱离实际。
机器人实际上应该作为未来人类生活和工作中的帮手,但在盲目追求比赛的过程中,学生设计的产品越来越技术化,逐渐偏离了应用的根本目的。
校内机器人教育很“温柔”
对比起“野战”式的校外机器人教育,像丰台五小这样的校内机器人教育就显得“温柔”多了。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机器人项目负责人张军说,中国目前机器人活动开展得很火,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喜爱,可以说是因为实际需求而产生的机器人入校教育。在以前的信息技术课上,老师教的是如何使用计算机,但这已经落在了时代发展的后面,机器人课程成为一项新颖的内容,这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机器人在北京一部分学校已经进入了校本课程,覆盖更多的学生,也为人才的挖掘提供了机会。
例如乐高机器人,整体课程体系并不长,覆盖3到16岁的年龄段,课程学完了就结束了,如果重复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机器人教育的关键不是学会,而是会学。在学校看来,开展机器人教育是为了顺应时代步伐,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科技思维,甚至通过这种开放式的教育帮助学生成长。丰台五小的小凯就是机器人教育的受益者。
某日,郝劲峰接到校长的电话,要把一位叫小凯(化名)的同学推荐到他的机器人组里,问他愿不愿意接收。“王校长找我谈话,说有这样一个学生,爱打架,但是特别喜欢机器人,想参加我的机器人小组,问我能不能招收他。我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郝劲峰说。这个几乎只会用拳头说话的孩子让郝劲峰一度后悔招收了他,最后,郝劲峰决定用机器人“改造”他。

经过无数次的交流,为他创造帮助其他同学的机会,让他展示自己的强项,小凯在教其他同学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也找到了自信。有一次小凯的班主任急冲冲地来找郝劲峰问小凯去哪里了,因为已经一节课没有见到他了。于是他们一起去机器人教室一看,原来他做机器人太投入了,没有听到上课铃响。郝劲峰说:“原来我的这份付出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尽管这是一个个例,但这才是机器人教育应该达到的效果。
不过,虽然学校教育的引导方式是开发式的,但是需要教育部门将机器人教育体系做更为系统的指导和政策支持,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系统,而不是凭借证书来判断一个孩子是否是“人才”,这样才能进一步引导校外教育机构回到机器人教育的本质,而不是急功近利。但目前的现状却是,校外林立的机构把机器人教育引到了比赛的“不归路”上。
打通机器人教育渠道
中国机器人教育发展到今天已走过十多年的历程,但在国内有限的教育模式之下,这依然是一个小众化的教育领域。在美国,机器人教育课程已经进入了大部分中小学必修课程范围,并且拥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撑课程所需要的费用。同时,教育体系的贯通让地区内的大学对当地中小学负有直接的机器人课程教育责任,大学资源会深入到广泛的、低龄的学校教育中,不仅能为更多的孩子提供学习机器人的机会,也能及时发现人才,减少了人才筛选的繁琐程序。
张军介绍说,目前科协在积极引导大学优秀的教学力量对机器人教师进行更专业化的培训,有了更专业的老师才能使机器人课程在学校开展得更加顺利。一所学校能不能设立机器人课程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教师力量,同时,机器人课程需要较高的成本,也是学校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教育部门对教材和教学程序做统一的计划,甚至统一课本,这样才能形成规模。在此基础之上,有实力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同时也能成为大学人才的后备军。
在我们的脑海中,机器人就是人的样子,伸伸胳膊、伸伸腿,从事一些简单的机械活动,但在如今越来越智能化的生活中,机器人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洗碗机、洗衣机、擦地机器人等等。而机器人人才的培养也绝不会止于设计一个会自己设定水温和水量的洗衣机,而在于未来的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而这些在我们看来,是IT达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缺少懂机器人和懂机器人教育的人才。
施宏伟说,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软件才是竞争的核心,硬件可以用3D打印来制作,而软件是必须由人脑来“制造的”,把人的思维通过软件表达出来,让物品代替人去做事情。
机器人教育更应该有完善的教育制度来保证,从中小学阶段开始渗透,就像当初的计算机一样从娃娃抓起。掌握制造和使用机器人的基本知识,在现在来看是特长,在未来来看应该成为一种必备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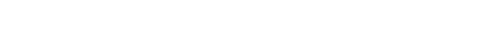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