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科学传播的优势与不足在哪?
受访者:贾鹤鹏,科学记者+科学传播学者,康乃尔大学传播学系在读博士,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 2011-2012年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发表了近1000篇新闻报道作品和20多篇(部)科学新闻与科学传播领域的论文和论著。
采访人:洪广玉(首席记者)

2015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上,家长带着孩子通过VR眼睛观看分子结构
中国科学传播的关键问题在于动力不足
北京科技报:您如何看待我国科学传播的现状?
贾鹤鹏:从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的科学传播发展非常迅速,强有力的国家动员体制在科学传播中也得到了体现,这种体制所拥有的庞大体系和资源是任何其他国家的科学传播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中国从事科学传播的目标和动力更倾向于科研宣传、国家战略宣传,与媒体公众以及与一线科学家脱节的情况仍然存在。举例来说,中国每年都会开展不同形式的科普活动,然而,参加活动的都是“跑口”记者,参加每个活动的记者大约只有几人到几十人。而美国科学促进会或美国化学会的年会,动辄就会有1-2千名科学记者报名参加,不需要跑口记者,只要证明自己是科学记者或自由撰稿人即可。近年来,美欧国家科学传播工作对科学家和科研过程影响越来越大,主流科学家对此都很重视,但我国的科学传播往往由退休或临近退休的科研人员担任,或者被委派给新入职的科研人员,只有在个别领域才有大腕科学家亲历亲为。
总体来说,中国科学传播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就,有很多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地方,但在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相关成员参与积极性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
北京科技报:中国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困境在哪? “科学传播”有“国情论”吗?
贾鹤鹏:我倾向于使用“科学传播的不足”来形容中国的状况。相比发达国家,我们最大的不足是科学界在进行科学传播方面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此外,应对科学争议越来越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工作,但这方面中国的科学传播体制有严重缺陷。
我想这方面的缺陷和体制、文化都有关系。我国的科研预算在形式上不需要向公众负责(西方也同样是专家决策,但在形式上,或者在大工程上则需要国会或议会等民意代表机构审批),这就导致了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没有动力把科学传播作为核心工作,最多不过将其作为形象展示。
我们的科学传播行为也与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儒家传统主导的中华文化并不重视总结自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重视形式逻辑,包括中医在内的一些文化传统所倡导的与现代科学相矛盾的做法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等,这些深深嵌入民族潜意识和行为习惯的文化烙印肯定会影响到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科学的接受、认知与传播。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在缺乏激励机制且竞争性科研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总是缺乏直面公众的动力。
公然宣称“反对科学”的声音值得警惕
北京科技报:如何看待应对争议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方面?
贾鹤鹏:在一个国家里,当科学在话语上越来越成为决策的依据,就会导致质疑政策和制度也会投射到科学上,进而,不同的政策群体也都会借助“自己的科学”,这就会形成科学与科学之间的话语竞争。此外,科学界内部本来就存在正常的争议,在传统上,这种争议本来是公众看不到的,但随着传播技术的发达,随着社会多元化,内部争议者有时会让这种争议外部化以获得公众支持。
这些情况在世界各国都会出现,但我们的体制因素和社会转型的国情决定了很多科学争议更容易突发,如最近的山东疫苗事件导致了人们对疫苗接种的质疑;中国社会对体制的不信任也会投射到科学争议上;最后,中国的科学传播体制特别难以及时应对科学争议,因为我们的体制构成的主体动因是宣传科技成就,而且体制导致了官员本能地推卸责任,即便官员出场,其公信力也不足以解决争议。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当前的“批判科学”,和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反智主义”有可比性吗?
贾鹤鹏: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确实出现过对科学的普遍质疑,它们是和反战、反核、反工业污染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阶段的公民运动,催生了学术领域对科学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目前的“批判科学”与西方60、70年代的情形很类似。但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原创思想,而且在学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英美的批判科学的学者是将自己居于一个认识论的中立立场,即并不必然认为(主流)科学认定的内容就是真的,但也并不必然反对科学,而中国的部分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者,则公然宣称反对科学,更有甚者把科学家有利益等同于科学家是特殊利益集团,不排除有阴谋,所以需要警惕。事实上,科学家作为人当然有个人的利益诉求,科学家作为群体当然有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而推导出反科学的结论,不能不说是逻辑混乱。
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我觉得真正需要担忧的是对科学的批判主导了科学传播的实务,或者是主导了人们的认知。比如转基因、比如PX、比如疫苗接种,我觉得公众对它们的顾虑都是很正常的,我不认为在科学问题上决策权应该归属于嗓门大的一方,但在这些领域,对科学的批判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强的作用,而公众并不能分辨出哪一方是科学,其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剥夺公众享有特定科学进步的权利。
应鼓励科学家们踊跃走入公共空间
北京科技报:如何看待科学争议中的公众参与?
贾鹤鹏:科学争议是科学传播中的正常组成环节,预防科学争议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而在科学争议爆发后,试图彻底消除争议也是不现实的。
在涉及科技争议的传播过程中,公众参与科学、与公众进行科学对话无可避免。我们要在态度上认识到包括微博民意在内的公众对科技争议的诉求,背后体现了民众真实的关切和对垄断性权力的抵制,它们为科学界与公众、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也要承认,包括微博民意在内的公众呼声绝不能被赋予颠覆科学权威的权力。
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民主原则,首先应该体现为公众对科学议题的恰当关切和对科学议程的合理设定,尤其是在涉及科技争议时。比如公众对转基因的质疑不能颠覆转基因的科学结论,但却可以合理地引导转基因安全研究获得重视和优先性。公众参与科学的民主属性也应该体现为民众及其代表对科学组织和科学行为的监督。这种参与既有科学的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化解科技争议的合理性。
北京科技报:您对科学家有何建议?
贾鹤鹏: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涉猎广泛的科学知识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树立一种信任科学和信任科学家的信心和寻求科学知识的动机。公众参与科学很有必要开展下去。其实这更多地应该作为一种方向和法理必要性,而不一定是事事都需要开展公众辩论的形式。如果广大科学家经常愿意经常走出象牙塔与公众、媒体交流,而不是把科普讲座固定在特定时间(科普日、科技周)特定的场所(科技馆)走过场,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公众参与科学。
科学家们踊跃地走入公共空间,人们更容易把对科学的潜意识的信任与对具体科学结论的接受联系起来,更容易信任科学,这也是科学传播的一个机会。
值得借鉴的是西方的科学传播体制化措施

NASA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帮助科学家、员工提升与公众沟通的能力技巧(图片转自NASA)
北京科技报:关于科学传播的实践,美国及整个西方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有哪些?
贾鹤鹏:如果说值得借鉴,那就是科研工作者或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体制化措施。这不仅仅是国家规定,也涉及到基金的分配,科研机构的鼓励和支持措施,以及科学家同行的鼓励和包容。此外则是社会机构和商业性机构对科学传播的参与。
从体制化的角度,往往是各种措施合在一起产生合力。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很多常规项目(中国自然科学基金成为面上项目)有做公众教育的要求,特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一般不会超过5%,通常比此低)要花在这上面。这种制度安排与中国政府资助专门的科学传播机构不同之处在于让科研团队有动力来从事传播。但仅靠政府层面上的政策安排还不够。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很重视科学传播,雇佣了很多科学记者,为科学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比如我所在的康奈尔大学,粗略估算一下,校方和各院系的传播团队(作为研究型大学,他们是科学传播的主力)至少有30人,这些人很多是专业科学记者,兼职供职于大学,以类似咨询公司的形式为科学家团队提供服务。
还有核心的一点,通过科学传播,科学家是有收益的。不论是发表论文、论文引用数还是基金获得情况,都有经验研究证明这一点,最后这一点也特别需要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者探究。

英国是科学传播工作的发源地,每年各地、各个机构都有很多科学活动。图为2014年英国爱丁堡国际科学节上,孩子们正在科学界志愿者帮助下,剪裁各种科技标志(来源:爱丁堡国际科学节组委会)。
北京科技报:您能否再介绍一下西方科学传播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
贾鹤鹏: 目前科学传播的各大传统正处于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过程。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从理论上颠覆了科普所体现的科学一方的霸权,提倡公众参与科学模式,但在过去10年来,欧美各国普遍开展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并不算十分成功。公众往往并不领情,参加各种活动很不踊跃。此外,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等方面,公众参与科学都存在很多问题,目前业内也在对其进行反思。
另一方面,主流传播学者遵循着传播效果研究的道路,发现了大量与人类认知行为相关的传播规律,很多规律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人类注意力有限这一基本前提上。他们正在以“科学传播的科学”为旗帜,大力在科学传播领域检验和发展这些规律。从2012年开始,美国科学院连续两年召开了“科学传播的科学”研讨会,其参加者主要是传统传播学领域的探究传播效果的研究者。
多年的研究表明,单纯传播知识并不能决定公众的科技态度,因为人们的认知因素,情感、注意力、信任、收益感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知识只是其中一环。而且在科学传播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科学对象上,科学知识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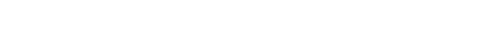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