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黄土高坡的古人类
记者/刘辛味 编辑/丁林 校对/肖园
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又提前了?7月11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家在黄土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在陕西蓝田县上陈村发现了距今212万年的石器工具,比公认的非洲之外最古老的德玛尼斯古人(185万年)提前了27万年。古人类迁移和扩散的经典模式可能会被改写。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朱照宇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在我国陕西省蓝田县上陈村一带发现了一个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在这片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北麓的遗址中的17个黄土-古土壤序列原生层位中,已经发现了96件石器,这些旧石器早期的产物涵盖的年代从126万年到212万年。
此前国际公认的非洲以外最早的古人类(直立人)遗址位于格鲁尼亚的德玛尼斯(Dmanisi)。科学家在那里挖掘出了距今185万~178万年的人类化石和石器。中国的新发现比其提前了27万年。

中国还有比元谋人更早的古人类?
陕西的新发现,是否能真正地把人类离开非洲的时间提前?在这项研究之前,中国最早的古人类记录距今大约170万年,也就是出现在我们历史课本上那两颗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还有比元谋人更早的古人类?
其实,我国距今200万年左右遗迹的发现不止这一次,在我国就有多处遗址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左右的石器。例如在重庆龙骨坡洞穴沉积物中发现了旧石器,在安徽繁昌人字洞和湖北建始县的洞穴遗址均被认为距今都有200多万年。本次论文通讯作者朱照宇表示,这些遗址所含有的人类活动遗迹的沉积物多属于“洞穴堆积”,沉积作用较为复杂,不太连续,测年技术比较复杂,所以存在着争议。他说:“据我有限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尽管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但在国际上始终存在着争议。”
科学上认定一个人种的出现,要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其一是找到能够证实物种的化石。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人类学家John Kappelman表示“只需一根手指骨就可记录人的存在”,但人类古化石极其罕见。二是给出相应的地质学证据。
虽然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科学家已确定了几个人种,但至今仍不能明确界定这些不同人种的骨骼特征。而从地质学定年的角度看,年代学上可能会有数十万年到数百万年的误差。对于地质历史来说,几百万年或许只是个小误差,但这对于仅存几百万年的物种,这种误差范围过大。另外,对于第四纪(距今约258万年)以来的沉积物定年,还没有一种绝对可靠的方法。
所以,要认定一个新的人种,或是判断他们何时走出非洲都十分困难。国内的几处遗址,要么缺少古人类化石,要么石器类型有争议,同时有定年上的问题。所以尽管有古生物化石的证据,但“超过200万年”的诸多遗迹都没能得到国际广泛的认可。
这次朱照宇研究团队能将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上,也经历了重重考验。“我们的论文在2016年12月投稿,历时一年半时间,经过了5次正式修改,20多次自己的修改才被接受。”尽管他们的团队也未发现古人类化石,但他们在遗址黄土的断代和原地埋藏的石器——人类活动的一个直接证据——给了他们一个较为明确的时间,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能被承认的主要原因。即便如此,朱照宇清楚“还是会面对很多质疑” 。

▲世界上已知的古人类遗迹分布 (来源:《自然》)
与蓝田遗址一衣带水的发现
陕西的黄土通过“古地磁定年”能很好地测出年代。目前公认的黄土沉积主要成因是“风成说”:黄土颗粒经过长距离的风力搬运,在特定的环境下(如我国的半干旱环境)堆积而成,堆积高达数百米,形成众所周知的黄土高原。黄土的堆积是连续的,不同年代的黄土和古土壤一层层叠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剖面。朱照宇的团队正是在位于黄土高原的灞河北岸,发现了黄土和古土壤的连续剖面——上陈遗址。
在灞河对面的南岸,就是曾经发现“蓝田人”的遗址。新剖面的发现,和蓝田人遗址不只是地理位置上靠近而已。

▲上陈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和兽骨(来源:《自然》)
1964年,科学家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发现了“蓝田人”头骨。这块蓝田人头骨最新的年代测定是朱照宇团队完成的——距今约163万年。这比之前测定的115万年还久远很多。他们在地层中还发现了石器,于是想到这里应该还有更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可惜公王岭的遗址剖面有缺失而不连续,他们就向周边寻找,结果在附近路上发现了一条红白黄相间的剖面,是一处典型的黄土-古土壤剖面。标志层如此明显,又发现了其中有石器,这令他们非常兴奋。
为了给出更加精准的测定,研究团队的工作长达十余年。从第一次踏上公王岭,到测出最古老地层是212万年,再到发表论文已经过去了14年。“2007年7月18日发现了上陈遗址,每年都去两三次,采样带回来测试”,朱照宇说。长期的坚持工作最终有了这项漂亮的研究成果。
上陈村陡峭的土层没有让任何一位参与者幸免——他们都摔过跟头。当吴翼博士认为野外作业十分辛苦时,朱照宇研究员说:“冬天极冷,夏天像蒸笼,但这些困难我们都可以通过毅力克服。” 已经年近七旬的朱照宇研究员还工作在科研一线,在他心中,作为地质学者的辛苦是“可以解决的困难”。朱照宇笑称,“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古人类在86万年跨度里反复在此居住
朱照宇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在野外勘察认清黄土后,与古土壤标志层进行对比、建立土壤地层序列,同时对黄土进行粒度分析、化学分析和矿物分析以确定为风成沉积物,发现与典型黄土一致。再研究这些沉积物是否可用岩石磁学的方法进行定年测试(发现适合),最终得到了距今的年代。
古地磁定年是地质学定年的重要方法。沉积物中的磁性颗粒形成时受地磁场的磁化,保留了当时的地磁场方向。地质历史中,地球磁场极性会发生倒转(北极变成南极,或相反),现在已经准确知道地磁场倒转的时间。对比地层中地磁场方向的倒转序列与地磁倒转的标准时标,就能得到地层形成的年代。
团队中主要负责古地磁定年的吴翼博士介绍,学术界内中国黄土磁性研究是比较成熟的,1982年时《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黄土奠基性的磁性地层序列,2002年建立了经过古地磁定年和粒度标定并使用天文轨道调谐的黄土模式年代序列,“黄土的古地磁测定和模式年代得到国际公认”。研究团队对黄土进行了高密度高分辨率的古地磁定年分析后,建立了上陈剖面古地磁年代学序列,与标准值对比得到了很好的时间年代——顶部第五层的40万年,到下部28层的214万年,而且这20多个层位里发现了旧石器。论文中主要介绍了古土壤层S15(Palaeosol,S)到黄土层(Loess ,L)L28的情况,时间跨度从126万年到212万年。这表明在距今126万年到212万年的长达86万年的时间里,黄土高原就有早期人类反复(不一定是连续)居住。
为什么选择古地磁定年,而不用其他的测年方法,比如人们常听到的同位素测年法?吴翼博士解释:“对沉积物的定年方法有很多,但像同位素、光释光等方法年代上限达不到要求,碳同位素定年只有3万-5万年。也有近年来发展比较好的铝铍同位素定年,但这种方法对样品要求很高,黄土里缺少能够测定的物质,所以也不能使用。”
这些古老石器属于谁?
因为此次的新发现与蓝田人遗址十分接近,是否这些石器是蓝田人(直立人)留下的?朱照宇给出了严谨的回答,“蓝田人是公认的直立人,但从年代上看,他们远早于目前认定直立人(德玛尼斯人)离开非洲的时间,所以是什么人种还不清楚。上陈遗址没有找到古人类化石,所以是不是直立人制造了这些工具,或是其他古老的人种(比如能人),还要进一步研究。”
朱照宇同时表示,他们通过地磁定年对比发现的石器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上陈村出土的96块石器,主要是奥杜威石器类型,也有小部分属于更后期的阿舍利(Acheulean)石器类型。这里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钻孔器和石锤,还有手镐和阿舍利文化中的两面器等。
什么是“石核”?两个鹅卵石互相敲击打磨下很多石片,原来的鹅卵石就有很多凹陷,也就是石核。石核继续加工成为“砍砸器”,可以用来砸东西。打磨下来的石片也可以继续加工,成为“刮削器”,它们比较锋利,可以用来割肉。另一些石片可以加工成“尖状器”,一些较为锋利的石块,被猜测为是绑在木棍上,当成矛等武器使用。
科学家如何认定出土的石器是人造工具?一方面,这部分黄土是本层堆积,非常完整,土壤十分细腻,而且周围也没有河流沉积物,所以可认定这些工具本不是原始就存在的。另一方面,石器本身有明显的锐化现象,在未打磨的地方还有原始的风化表层,而打磨过的缺口相对新鲜。这些石器形状最小直径几厘米,大的有几十厘米——只能是人工制成。团队认为,这些石头原本可能来自秦岭山麓。
团队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些不完整的动物化石,包括远古的牛、羊、马、猪和猎狗、剑齿虎的牙齿。虽然我们可以猜测,古人用工具处理过这些动物的尸体,但研究团队出于严谨并未在论文中给出相应的关联。John Kappelman认为,骨头上是否有切痕,被人为破损的标记,或是石器上检测出微生物标记可以作为证据。不过,团队目前已经发现的遗骸都是残缺的,并且在黄土中风化严重。想要做出关联判断,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左图:研究者在陡峭的山坡上作业;右图:出土的石器 (来源:纽约时报)
考古研究不只是“比谁最老”
到底是谁最早走出了非洲,最先拿起了工具?
目前为止,全世界发现古人类遗址的时空分布不连续,这极大地限制了人类演化的研究。而朱照宇团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全球变化下的黄土-古土壤序列和古人类的演化能够联系起来。在团队重点研究的17个包含石器的黄土-古土壤地层中,11层古土壤指示了暖湿气候期,6层黄土指示了干冷气候期,这反映出:早期人类可能比较适应暖湿的气候环境。
距今260万年以来,世界至少经历了33次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换。黄土能够连续地沉积下来,但人不一定能够连续在这里居住,可能有反复迁徙——这让亚洲对于人类进化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地质学和古人类学结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为不同层之间的石器,可能揭示了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朱照宇认为,“中国黄土高原是研究古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天然试验场,它开拓了黄土-古土壤序列和古人类文化演化序列研究的新途径,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早期人类起源、迁徙、扩散、演化的经典模式。” 对于未来的工作,朱照宇表示还要继续更广泛地调查,希望找到古人类的化石遗骸,找出他们居住的场所,探索那些动物是不是他们狩猎的。
长久以来,我们在宣传考古发现时,总是注重“最先”“最老”等具有轰动效应的成果,“并不太重视内涵和意义。”朱照宇告诉记者,“过去我们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老师写过不少科普文章,但年轻一代写得不多,不太注重这方面,应继续改进。我们应该注重科学本身,而不是它所能引发的公众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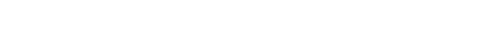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微信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
北京科技报客户端